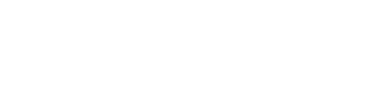【早安健康/韓慶銀(心理諮商研究員)】
電影《邊山》中,善美正在照護生病的父親,幫他處理大小便。當父親弓著身體說:「我大便了」的時候,善美忍耐的保險絲徹底斷了線。其實,善美是一個心地善良且懂事的孩子。至今為止,她不僅細心照顧父親,出於惻隱之心還會幫忙照顧隔壁床的病人。可以說,善美是一個「善良的女兒」。為什麼這樣的她會在幫父親處理大小便時,突然不耐煩呢?善美擺著臭臉,用地道的方言表達不滿的場面令我感到痛快不已。
之後沒多久,雖然沒有像善美那樣火山爆發,但我也顯露出自己的「冒失」。
在對別人負責任和盡義務以前,應該把自己人生的獨立性和自發性放在首位。
「一天三次吧!哪有人一天大便六次的!」電影《邊山》中,善美正在照護生病的父親,幫他處理大小便。當父親弓著身體說:「我大便了」的時候,善美忍耐的保險絲徹底斷了線。其實,善美是一個心地善良且懂事的孩子。至今為止,她不僅細心照顧父親,出於惻隱之心還會幫忙照顧隔壁床的病人。可以說,善美是一個「善良的女兒」。為什麼這樣的她會在幫父親處理大小便時,突然不耐煩呢?善美擺著臭臉,用地道的方言表達不滿的場面令我感到痛快不已。
之後沒多久,雖然沒有像善美那樣火山爆發,但我也顯露出自己的「冒失」。
請勿設定超過兩組超連結
請勿設定超過三組超連結
請勿設定超過五組超連結
有需求書沒有需求書有需求書沒有需求書有需求書沒有需求書有需求書沒有需求書有需求書沒有有需求書沒有需有需求書沒有需求書有需求書沒有需求書有需超級連結!!!!!!!!!!!!!!!!!!!!!!!!!!!
測試資料請你複製URLhttps://media-sit.h2u.io/
「媽,我吃飯的時候,妳不要再提大便的事了。」
瞬間,我那命中註定要做的「孝女」光譜出現了裂痕。由於抗癌藥物的副作用,母親正因腸麻痺(腸子無法活動,粘連在了一起)而痛苦不已,所以我們聊的話題都是關於痛症、便秘、該吃什麼和不該吃什麼。正因為這樣,大便自然而然的成了日常生活中一個很重要的話題。但母親卻開著廁所的門大便,還不分場合的提起大便的事。其實,我不喜歡她開著門上廁所,也很討厭她吃飯的時候聊起大便的事。但轉念一想,她正在生病,所以只能忍下來。沒想到的是,那天我下意識地講出了自己的不滿。聽到我提出這種要求,母親一句話也沒說,看到她心裡很不是滋味,我也感到十分內疚。但即便是這樣,我還是覺得自己做對了。如果我不這樣做,早晚有一天也會像善美那樣火山爆發,或是跑去漢江做出極端的選擇。假如我一直壓抑自己的感情和欲求,扮演好女兒的角色,凡事順從母親,肯定會發生以下這些事。
—堅持包容母親訴苦的問題(完美女兒情結,善良人情結)。
—擔心如果提出要求,母親會不喜歡或是難過,所以不表露自己的欲求。當出現負面情緒時,選擇迴避。
—但我依然很討厭在吃飯時聽到詳細描述大便的事,而且產生了比之前更強的的抗拒心理(因為迴避會誘導更強烈的想法和感情)。
—隨著負面情緒越來越強烈,也會對未能遵守包容母親的承諾而自責。
—自責未能分擔母親的痛苦和未能掩飾自己的不滿。
瞬間,我那命中註定要做的「孝女」光譜出現了裂痕。由於抗癌藥物的副作用,母親正因腸麻痺(腸子無法活動,粘連在了一起)而痛苦不已,所以我們聊的話題都是關於痛症、便秘、該吃什麼和不該吃什麼。正因為這樣,大便自然而然的成了日常生活中一個很重要的話題。但母親卻開著廁所的門大便,還不分場合的提起大便的事。其實,我不喜歡她開著門上廁所,也很討厭她吃飯的時候聊起大便的事。但轉念一想,她正在生病,所以只能忍下來。沒想到的是,那天我下意識地講出了自己的不滿。聽到我提出這種要求,母親一句話也沒說,看到她心裡很不是滋味,我也感到十分內疚。但即便是這樣,我還是覺得自己做對了。如果我不這樣做,早晚有一天也會像善美那樣火山爆發,或是跑去漢江做出極端的選擇。假如我一直壓抑自己的感情和欲求,扮演好女兒的角色,凡事順從母親,肯定會發生以下這些事。
—堅持包容母親訴苦的問題(完美女兒情結,善良人情結)。
—擔心如果提出要求,母親會不喜歡或是難過,所以不表露自己的欲求。當出現負面情緒時,選擇迴避。
—但我依然很討厭在吃飯時聽到詳細描述大便的事,而且產生了比之前更強的的抗拒心理(因為迴避會誘導更強烈的想法和感情)。
—隨著負面情緒越來越強烈,也會對未能遵守包容母親的承諾而自責。
—自責未能分擔母親的痛苦和未能掩飾自己的不滿。
—越是自責,越是會迴避感受到內疚的狀況。
—覺得越來越難以跟母親一起用餐。
—對一起用餐感到不安,因此會一再迴避一起用餐。
—隨著與母親的距離變得疏遠,罪惡感也加重了。
—不光是罪惡感,由於壓抑自己的感情和欲求,因此加重了憤怒和受害情結。
—在經歷這些過程時,我會被自己疏遠,人生被流放。
為了避免眼下的內疚和不愉快而選擇忍耐,表面看起來似乎沒有矛盾,但從長遠來看這種對策並沒有效果。控制和壓抑感情和欲求,只會促使它們獲得爆發性的力量。屆時,為了阻止這種爆發性的力量,便需要更強的自我控制。這樣的過程終究會帶來痛苦和折磨。不光是對自己,對人際關係和社會也毫無幫助。因此,我放棄成為完美的、容忍的監護人。我換掉了那扇母親可以隨時進出我內心極限的「自動門」,取而代之換了一扇「需要手動開關的門」。對我而言,這是理所當然的事,而且為了我們的關係這也是一個正確的選擇。有時這樣做也會讓身邊的人失望和受傷,但任何關係都必然會存在矛盾。如果存在,也只是存在於單方面的或者壓迫性的關係。
希臘神話中的普羅克魯斯強迫過往的行人躺在一張鐵床上,如果那個人的身高不及那張床,便會拉長他的身體使其符合床的長度;如果身高超出那張床,便會斬斷多餘的部分。這個有名的「普羅克魯斯之床」的故事,象徵性的描寫出了那些按照自己的標準來操縱他人的邪惡。我們來套用一下這個故事,假如我們的內心存在一個犯下惡行的普羅克魯斯?
最終,那張「必須合適」的普羅克魯斯之床會成為囚禁我們的框架。躺在床上,是頭和腳正好符合床的長度舒服呢?還是留有一些空餘的空間舒服呢?當然是不管怎麼躺都可以躺下、留有足夠的空餘空間的床最舒服了。這就是適中和模凌兩可的美德和自由。
你需要的是絕對溫柔的愛人、絕對合拍的配偶、絕對完美的父母,以及成為做事完美的員工嗎?你夢想的是徹底的理解、溝通和人際關係嗎?這種絕對和徹底是指不多也不少,剛剛好的狀態。試想一下,一杯水在稍稍沒有填滿的狀態下,才容易拿起來和喝到水。不多也不少的完美狀態只會令我們痛苦。在無菌、絕對乾淨的環境下,我們會失去免疫力,甚至難以維持生命,就像沒有人能活著逃出普羅克魯斯之床一樣。
當別人提出要求時,不管是自己可以做到的,還是不願去做的,我們內心是不是都有「必須去做」的想法呢?雖然我們的內心深處很想與父母分離,去過自己的人生,但另一方面是否又在說服自己身為子女理所當然應該守在他們身邊盡孝呢?換作父母的立場,雖然應該讓長大的孩子獨立,但是否以「他還是個學生」、「孩子收入不高」、「等他結婚的時候」等藉口挽留著孩子呢?這都是按照社會的規則和習俗來設定自己的角色,把自己放入框架之中。從心理學的角度看,原因都是來自罪惡感、補償心理和依賴欲求。在扮演角色以前,自己的心境最為重要。如果比起自己的現實處境和心理狀況更在意扮演的角色,那只是要面子、做作和假面的遊戲而已。因此,情況不允許的話,就要靈活考慮扮演的角色。此外,在對別人負責任和盡義務以前,應該把自己人生的獨立性和自發性放在首位。這不是以自我為中心,而是不責怪他人的宣言,是一種對自己人生負責的態度。
我們不是渺小和微不足道的存在,反過來,也不是特別的、完美的存在。我們只是有著與生俱來的耐力,再靠努力培養耐力,以此付出行動和尋求改變而已。人生沒有理所當然的、固定的和必須照做的事情,越是沉迷在沒有瑕疵的角色遊戲裡,越是會遠離真正的自己。為了沒有對立與衝突、不和與矛盾的關係,越是會受到束縛,自己的內心越是會被疏遠和被孤獨糾纏。那些寧可疏遠與他人的關係,也不疏遠自己的人是不會受到外部矛盾而產生動搖的。所以請放心,守護好自己,保持與他人關係的界線。雖然這樣偶爾會覺得孤單,但絕不會拔掉自己的根基。
本文摘自《你不用看別人臉色也可以活得很好:果斷拒絕利用你的善良來剝削感情的人》/韓慶銀(心理諮商研究員)/幸福文化
看了這篇文章的人,也看了...
—覺得越來越難以跟母親一起用餐。
—對一起用餐感到不安,因此會一再迴避一起用餐。
—隨著與母親的距離變得疏遠,罪惡感也加重了。
—不光是罪惡感,由於壓抑自己的感情和欲求,因此加重了憤怒和受害情結。
—在經歷這些過程時,我會被自己疏遠,人生被流放。
為了避免眼下的內疚和不愉快而選擇忍耐,表面看起來似乎沒有矛盾,但從長遠來看這種對策並沒有效果。控制和壓抑感情和欲求,只會促使它們獲得爆發性的力量。屆時,為了阻止這種爆發性的力量,便需要更強的自我控制。這樣的過程終究會帶來痛苦和折磨。不光是對自己,對人際關係和社會也毫無幫助。因此,我放棄成為完美的、容忍的監護人。我換掉了那扇母親可以隨時進出我內心極限的「自動門」,取而代之換了一扇「需要手動開關的門」。對我而言,這是理所當然的事,而且為了我們的關係這也是一個正確的選擇。有時這樣做也會讓身邊的人失望和受傷,但任何關係都必然會存在矛盾。如果存在,也只是存在於單方面的或者壓迫性的關係。
希臘神話中的普羅克魯斯強迫過往的行人躺在一張鐵床上,如果那個人的身高不及那張床,便會拉長他的身體使其符合床的長度;如果身高超出那張床,便會斬斷多餘的部分。這個有名的「普羅克魯斯之床」的故事,象徵性的描寫出了那些按照自己的標準來操縱他人的邪惡。我們來套用一下這個故事,假如我們的內心存在一個犯下惡行的普羅克魯斯?
最終,那張「必須合適」的普羅克魯斯之床會成為囚禁我們的框架。躺在床上,是頭和腳正好符合床的長度舒服呢?還是留有一些空餘的空間舒服呢?當然是不管怎麼躺都可以躺下、留有足夠的空餘空間的床最舒服了。這就是適中和模凌兩可的美德和自由。
你需要的是絕對溫柔的愛人、絕對合拍的配偶、絕對完美的父母,以及成為做事完美的員工嗎?你夢想的是徹底的理解、溝通和人際關係嗎?這種絕對和徹底是指不多也不少,剛剛好的狀態。試想一下,一杯水在稍稍沒有填滿的狀態下,才容易拿起來和喝到水。不多也不少的完美狀態只會令我們痛苦。在無菌、絕對乾淨的環境下,我們會失去免疫力,甚至難以維持生命,就像沒有人能活著逃出普羅克魯斯之床一樣。
獨立性和自發性應放在人生的首位
我們不可能對他人盡善盡美,也不可能一直滿足對方的願望。因此,我們在下意識中也會傷害別人。我也是一樣。正因為無法得到全世界所有人的愛和認可,所以才會經歷失望和挫折。有時,比起做自己想做的事,我們更像是為了避免發生什麼而活,就像把不可能的事變得可能的生存遊戲一樣。我們依靠的牆本來就是傾斜的,但卻用盡渾身力氣想要扶正它。完美的水平和垂直只有十字架而已,就連地球也是傾斜二十三點五度在旋轉。當別人提出要求時,不管是自己可以做到的,還是不願去做的,我們內心是不是都有「必須去做」的想法呢?雖然我們的內心深處很想與父母分離,去過自己的人生,但另一方面是否又在說服自己身為子女理所當然應該守在他們身邊盡孝呢?換作父母的立場,雖然應該讓長大的孩子獨立,但是否以「他還是個學生」、「孩子收入不高」、「等他結婚的時候」等藉口挽留著孩子呢?這都是按照社會的規則和習俗來設定自己的角色,把自己放入框架之中。從心理學的角度看,原因都是來自罪惡感、補償心理和依賴欲求。在扮演角色以前,自己的心境最為重要。如果比起自己的現實處境和心理狀況更在意扮演的角色,那只是要面子、做作和假面的遊戲而已。因此,情況不允許的話,就要靈活考慮扮演的角色。此外,在對別人負責任和盡義務以前,應該把自己人生的獨立性和自發性放在首位。這不是以自我為中心,而是不責怪他人的宣言,是一種對自己人生負責的態度。
我們不是渺小和微不足道的存在,反過來,也不是特別的、完美的存在。我們只是有著與生俱來的耐力,再靠努力培養耐力,以此付出行動和尋求改變而已。人生沒有理所當然的、固定的和必須照做的事情,越是沉迷在沒有瑕疵的角色遊戲裡,越是會遠離真正的自己。為了沒有對立與衝突、不和與矛盾的關係,越是會受到束縛,自己的內心越是會被疏遠和被孤獨糾纏。那些寧可疏遠與他人的關係,也不疏遠自己的人是不會受到外部矛盾而產生動搖的。所以請放心,守護好自己,保持與他人關係的界線。雖然這樣偶爾會覺得孤單,但絕不會拔掉自己的根基。
本文摘自《你不用看別人臉色也可以活得很好:果斷拒絕利用你的善良來剝削感情的人》/韓慶銀(心理諮商研究員)/幸福文化
看了這篇文章的人,也看了...
延伸閱讀
繼續閱讀下一篇推薦文章